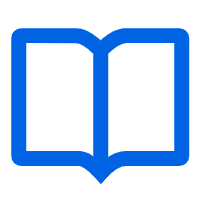中国画只是黑白吗?
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这话说起来轻松,可真正要怎么做、做多少,却很难有个量化的标准。于是有“传统”这杆大旗高高扬起,仿佛只要打着它的旗号,一切行为都有了合法的身份和美好的期许——尽管这个“传统”实际上可能早已面目全非。 于是有人拿它来标榜自己,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;于是有人用它来做挡箭牌,以掩饰自己的浅薄与无知;更有人将它视为至宝,奉为圣经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其实这是完全误解了这六个字的意思。“笔墨”不是指某个具体的绘画技法或工具材料——“笔”指毛笔,“墨”指水墨,这些难道还要再解释吗?“笔墨”指的是一种造型的语言方式,它是相对抽象的,并不能象照相机一样实指哪一个固定的对象。
所以,无论使用什么样的笔墨,都不可能“像”照相机一样确切的再现某一特定的客观景物。相反,正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可塑性,才赋予了中国画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:书写性。 中国画是写出来的(当然也有描画的),而不是“画”出来的。这一点,与中国传统的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正因为此,我们才能在古人的作品中看到那么丰富的笔墨变化。
然而这种丰富性并没有影响它们的“写实”能力。古人并不是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们的作品,他们并不追求画面的“生动逼真”,而是追求“气韵生动”,也就是说,他们在意的并非画面是否真实地再现了某一处实景,而是在画面上“作出意思来”——这个意思也许是作者的个人情趣,或者是观者的个人感受,但它必须符合“自然”的规律,否则就是“怪诞”了。
所以我们才能从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中看到一个美丽动人的“洛神”形象,虽然我们从未见过曹植《洛神赋》中的那个具体的美女;我们才能从赵佶的《瑞鹤图》上看到千姿百态、活泼可爱的丹顶鹤,虽然它们远没有真实的丹顶鹤那么大;我们才能从齐白石的《荷蟹图》感受到那种出淤泥而不然的清雅,虽然水中并未真正出现荷花的倒影……